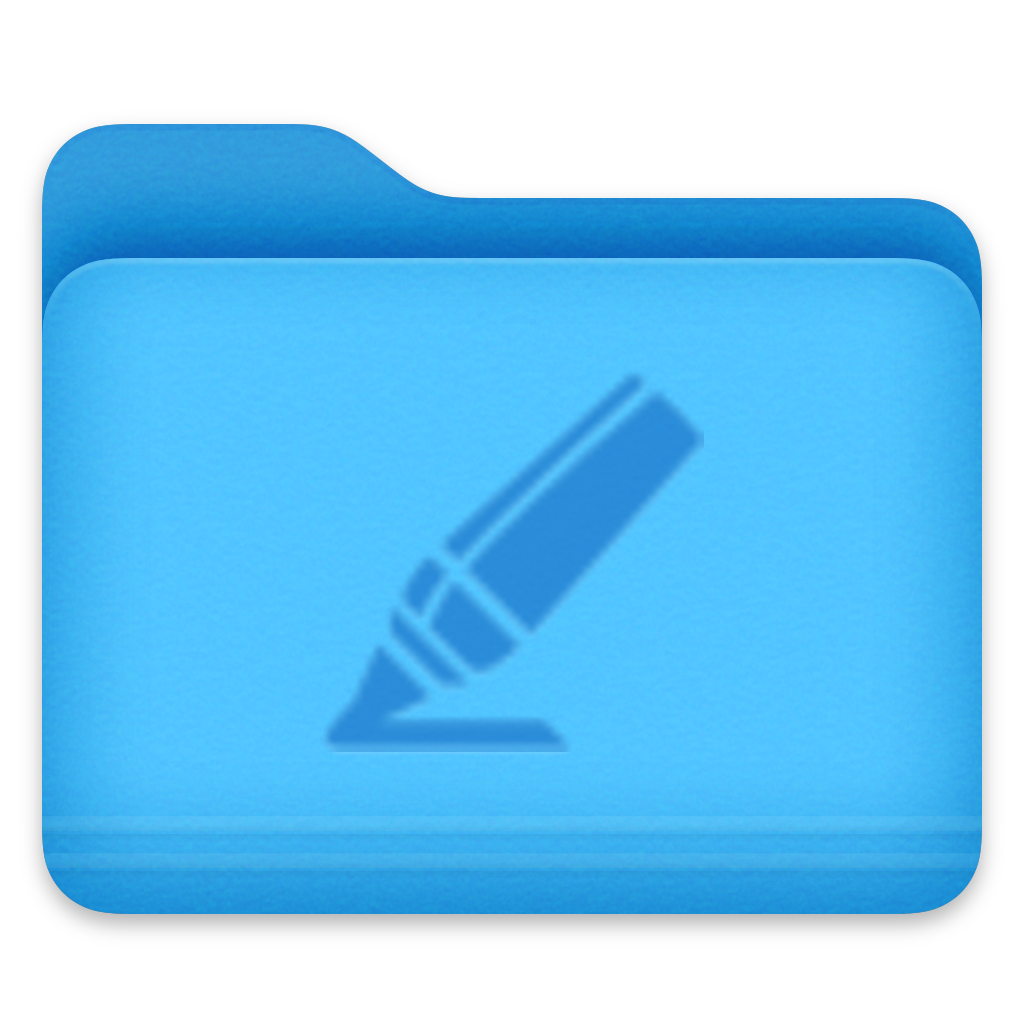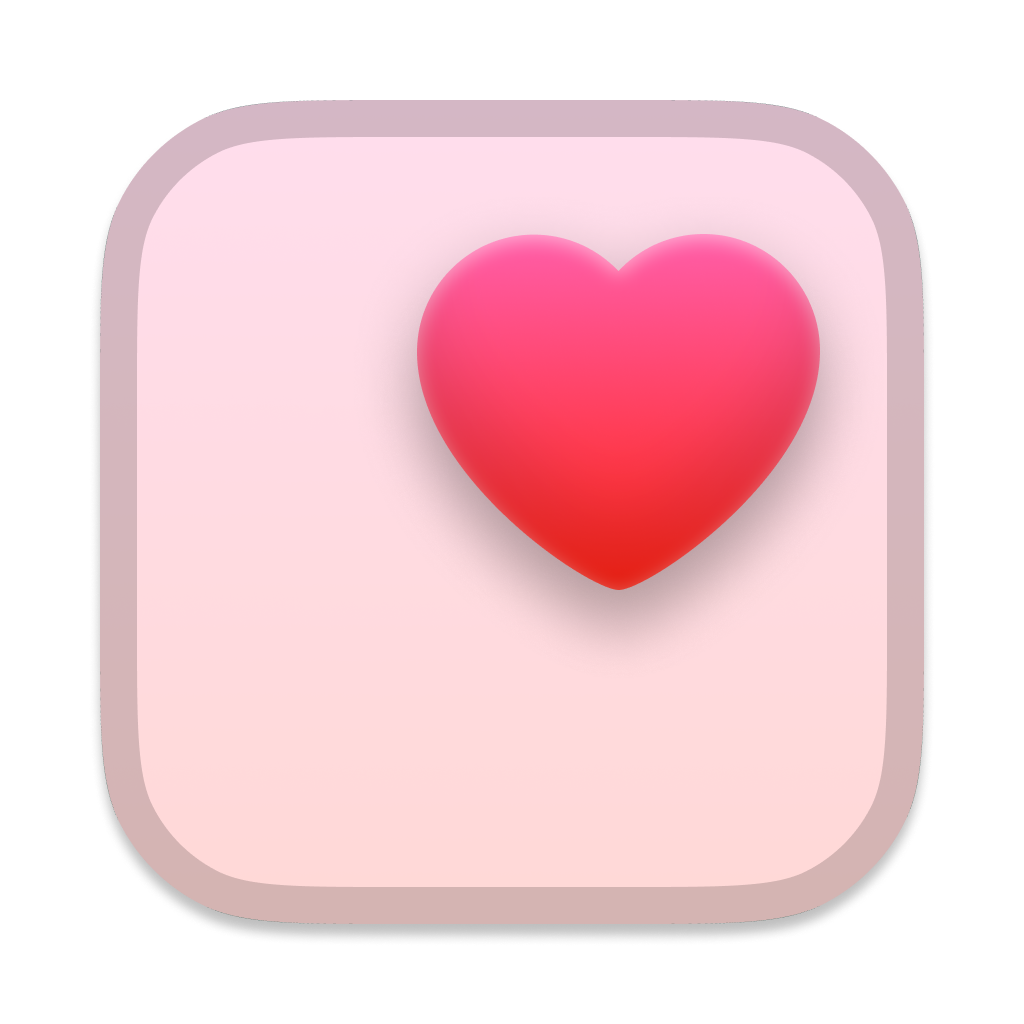学习资料
Mreddiehu - 介绍
苍井老师 - 英语
波多老师 - 数学
小泽老师 - 英语
吉泽老师 - 数学

身長:155cm
スリーサイズ:B90-W58-H83
ニックネーム:あおいそら、そらちゃん
趣味:読書、映画鑑賞、料理
主な出演作品:「蒼井そら エスワン」シリーズ、「蒼井そら プレミアム」など
1'30"
Mreddiehu
你好,我是 Eddie 👋
为什么要做这个网站
这是一片属于我的线上自留地,也是我与世界对话的小小窗口。在这里,你能看到我对生活的记录 —— 是街角偶然撞见的晚霞,是三餐四季里的烟火暖意;能读到我对学习的思考 —— 是探索未知时的困惑与顿悟,是沉淀积累后的心得与成长;也能感受到我对音乐的热爱。
项目
项目1:vocabkeep词萦 是一款涵盖多学习层次的记单词网页应用,帮助用户高效记忆和管理词汇的网站。
项目2:爱迪胡先生听写 是专业的英语听写练习平台,帮助提升听力和拼写能力。